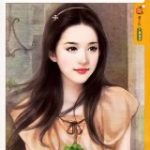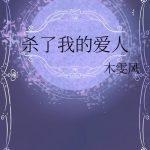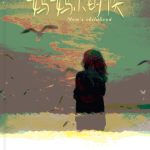疊翠尋迷
第二日,慕容琅和禦風主仆二人騎馬向樂清山疾馳而去。平日要行三天的路程,因他二人日夜兼程,兩日後的下午就到了山中。
夏日的樂清山,綿長的峰巒下林木蔥茏,古樹參天。頭頂上,枝梢交錯,綠葉繁盛,接連成片,宛如藍天下的一片碧雲,搖曳萬裏。耀目的陽光透過層疊的枝丫落于地上,斑斑點點。林中日影細碎,明暗交錯,山間溪瀑縱橫,流水潺潺,意境幽深空寂。有那麽幾個時刻,慕容琅不禁想起了自己年少時在卧雲谷春獵時的情景。
山路蜿蜒盤繞,間或蒼苔石徑。兩人騎馬緩行,大約半個時辰後來到疊翠庵門前。二人下馬,禦風輕輕叩門,不一會兒一個身着粗布僧袍的小尼姑開了門。
“這位小師父,我和我家主子是前來拜訪浸惠住持的。請問她可在庵中?”禦風恭敬地說道。
“阿彌陀佛,住持正在閉關,不見外客。”小尼姑雙手合十道,說罷她上下打量了禦風一眼,繼而又道:“诶……這位施主,你……你是不是幾日前來過?”
“小師父好眼力。前幾日我确實來過,這次是陪我家主子一起來的。我家主子姓……姓張,是在京城做買賣的。”說罷,他看了眼慕容琅。慕容琅點了點頭。
小尼姑又問:“不知兩位施主此番前來,所為何事?”
“是有關我家主子的一個遠方親戚,名叫蘇五斤。十幾年前,他被送到了疊翠庵,後來就沒了音訊。上一次我來便是為了此事,但我回去禀明後,我家主子想再求見住持一面,故而不得已又來叨擾了。” 禦風拱手道。
小尼姑有些為難:“可浸惠住持閉關時是不能打擾的,二位還是請回吧。”
禦風一滞,正思忖着該如何回應。這時,慕容琅款款走了過來。小尼姑見此人金冠束發,玉面劍眉,星眸鼻挺,姿容氣度不似凡人,身上還帶着一股似有若無的松香,就像山中的清風一樣醉人,不由看呆了。
只聽慕容琅聲如玉石,向她言道:“這位小師父,在下要尋的蘇五斤乃我家一位重要親眷,因失蹤多年,家中甚為憂慮。都說出家人以慈悲為懷,還請小師父幫忙向住持通傳一聲,在下感激不盡。”說罷,便拱手躬身施禮。
小尼姑聽面前這位公子自稱“在下”,又向她欣然施禮,十分謙和,不禁面上一紅,羞怯地說道:“那……那請二位稍後,容我去試試。”
小尼姑走後,禦風偷偷看了慕容琅一眼,心想:“主子這張臉好使自己是知道的。只是沒想到連出家人也吃這張顏。哎……主子說出家人以慈悲為懷,那出家人還應該六根清淨呢……”
大約過了一柱香的時間,庵門終于開了。小尼姑向着二人雙手合十,道:“阿彌陀佛,讓兩位施主久等了。住持命我帶兩位進去。”
慕容琅道了聲謝,便跟在小尼姑身後,邁步進入庵中,禦風跟在後面。疊翠庵不大,坐西朝東,依山勢而建。有殿三進,分為前、後兩院。前院有山門、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大悲壇、放生池、鐘樓和鼓樓,南北兩側建有配殿。後院建有主殿及南北配殿。
庵中建築因年久失修,朱漆褪色,壁畫剝落,但并沒有破敗頹然之态,反而更添了古樸清幽。庵內未見香客,只有寥寥女尼靜默穿行。放生池中一波碧水倒映藍天,幾尾錦鯉悠游其中,有種超然離世的意境。
慕容琅來到客堂坐等。片刻後,一位三十多歲的師尼緩步而來,身後跟着剛才引路的小尼姑。師尼身着黃色海青,頭戴僧帽,手握一串檀香佛珠,神色安谧。她見到慕容琅,微微颔首,端然坐下。小尼姑為二人奉上茶水,随後便退了出去。禦風則守在門外。
慕容琅猜到此人正是住持浸惠,便起身拱手行禮道:“在下張逸之,見過住持。”
浸惠住持雙手合十回禮:“阿彌陀佛,施主不必多禮。”言畢,示意慕容琅入座便可。
“聽聞張公子是來打問本庵曾經收留的一位孩童,名叫蘇五斤的消息?”浸惠住持問。
“正是。他是我家的一位遠方親戚。”慕容琅回答,随後欠身道:“聽聞住持正在閉關,然此事對在下甚為重要,冒然前來,打擾住持修行實屬無奈,還請您見諒”。
浸惠住持語氣和緩:“事關張公子家人,貧尼自然理解。只是貧尼來到疊翠庵不過短短數年,關于這個孩子的事,貧尼雖知道一些,但更多是從前任住持淨慈師太那裏聽來的。”
慕容琅聞言,眸中一亮:“這麽說,住持是知道蘇五斤的?”
浸惠住持慢撚佛珠,平靜地說道:“聽淨慈師太說,十幾年前蘇五斤的父親抱着他來到疊翠庵,請求淨慈師太醫治這個孩子,并希望留他在庵中修行一段時日。那時蘇五斤還不到兩歲。淨慈師太聽着這個名字實在不像話,便想為他改一改。因他父親希望孩子長大後,不要學自己是個殺豬的,而是做個讀書人光耀門楣,淨慈師太便為他改名‘蘇墨’。”
她喝了一口茶,繼而又道:“當時,蘇墨應是從娘胎裏帶了一股惡症,骨瘦如柴,身子極為虛弱。雖說能夠醫治,但需花費很長時日,湯藥也不能斷。他父親便懇求淨慈師太無論如何将孩子治好,并放下五十文錢,說好以後每月都會過來送藥資。”
“然而大約過了半年,漸漸的他父親來的就少了,一年後就再也沒有出現。淨慈師太心慈好善,便将這個孩子收留了下來,經過幾年的悉心調養,終于治好了他的病。此後,蘇墨就跟着淨慈師太在庵中修行。”
慕容琅認真聽着浸惠住持的講述,随即問道:“那這位蘇墨如今可還在庵中?”
浸惠住持搖搖頭,語帶苦澀:“想必施主也看到了,疊翠庵平素香客甚少,香火寡薄,生活極為清苦。幾年前,淨慈師太向周邊村中的農戶募集了一些銀錢,分發給年老體弱的女尼,讓她們下山各自返家。如今庵中只有十來個女尼,每日需靠耕種勞作養活自己。淨慈師太圓寂後,蘇墨就下山了,一則他已經長大,身為男子留在庵中多有不便,二來他也該出去闖一闖,不能在疊翠庵荒度一生。”
“那您可知他去了哪裏?”慕容琅又追問道。
“他臨行前,說是會去京城。餘下的,貧尼就不清楚了。”浸惠住持撚着佛珠,眸色安寧。
慕容琅不語,思忖了片刻,随後從袖中掏出一張畫像,起身送至她面前,道:“請住持看看,可否見過此人?”
浸惠住持接過畫像,展開一看:“這不是蘇墨麽?”
“哦?您确定他就是蘇墨?”慕容琅确認道。
“确定!這麽清秀出塵的少年除了他,我還沒見過第二個。”浸惠住持答道,看向慕容琅。
慕容琅心下了然。
浸惠住持見二人已敘話多時,便起身,雙手合十,道:“阿彌陀佛!貧尼已将自己所知都告知與施主。如施主沒有其他想問的,恕貧尼就不久留了。”
慕容琅聞言心知這是送客的意思,便躬身深施一禮,道:“多謝住持為逸之解惑。今日在下多有打擾,望您海涵。”
浸惠住持又念了一句佛號,便喚來剛才的小尼姑,讓她将慕容琅主仆二人送出庵中。
慕容琅離開前,讓禦風捐了一百兩銀票的香火給疊翠庵。小尼姑接過銀票,恭謹道謝。二人旋即策馬消失于山林間。
疊翠庵正門旁的一條石徑小路上,露出一角灰色僧袍,一位帶發修行的師尼望着他們遠去的方向,默默不語……
日暮西垂,晚霞豔麗,為樂清山平添了一抹絢爛。林中光線漸暗,鳥獸歸巢,比來時多了幾分神秘。慕容琅和禦風打馬在山道上前行,待轉過幾個彎,再回首時,只見疊翠庵已沒入了密林,僅留一角屋檐。
“果然是個避世的好去處。”慕容琅暗道。他一邊行路,一邊将浸惠住持的話給禦風講了一遍。禦風聽完,拍了下大腿,爽朗地道:“這麽看來,那位蘇公子應該就是沣水縣的蘇五斤了。”
慕容琅聞言,嘴角上揚,嗤笑一聲道:“禦風啊禦風,沒想到這些話連你也給騙了去!”
禦風一愣,不解地看着慕容琅:“騙?主子何處此言?”
慕容琅目視前方,眸色深沉:“謝府上的蘇墨就是淨慈師太的義子,這一點通過浸惠住持對畫像的指認已毋庸置疑。至于蘇墨就是蘇五斤,哼!簡直就是無稽之談!”
禦風皺起了眉頭,有些納悶:“可我覺得那位住持說的沒什麽問題啊。”
“沒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!”慕容琅的語氣不容置疑:“你想想,一個屠戶的兒子,在疊翠庵生活了十幾年,與京城沒有半點幹系。如果說,他下山後,寄居謝府是憑着淨慈師太與謝鴻的關系還情有可原,但他闖進我父親的書房,這又是為何?”
“也是。”禦風撓撓頭,困惑地道:“這麽說的話,确實講不通。”
“據我揣測,當年疊翠庵中除了蘇五斤,應該還有另一個孩子。真正的蘇五斤已經死了。他死後,這個孩子頂替了他的身份,變成了如今的蘇墨。所謂的遣散衆尼,恐怕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掩蓋當年的秘密。”慕容琅冷冷地道:“淨慈師太要麽沒對浸惠說實話,要麽,就是浸惠在刻意隐瞞!”
禦風恍然大悟:“那是否需要屬下将浸惠住持抓來審問?”
“不必!”慕容琅眼中生出一絲狠厲,聲音中似含了寒冰:“此事不知是否還有他人牽涉其中,這麽做只會讓他們有所警覺。命暗衛嚴密布防疊翠庵,如有異動,速速回禀!”
“是!”禦風抱拳回道。